

一般用硬笔写点画,心里想好,用手表现并不算难。但是换用毛笔、墨汁、宣纸,要表现心里的点画,对初学来说便很不易。因为毛笔软,宣纸松,水墨一入纸,迅速渗透,很难控制。多数人初学,都会出现诸如“钉头”、“鼠尾”、“蜂腰”、“鹤膝”等出乎意料的点画。笔瘫软在纸上像条死蛇,要提提不起,要行行不动,很令人丧气。许多人经不起折腾,耍几下便再也不想摸毛笔了。甚至还会埋怨祖先,为什么要用毛笔写字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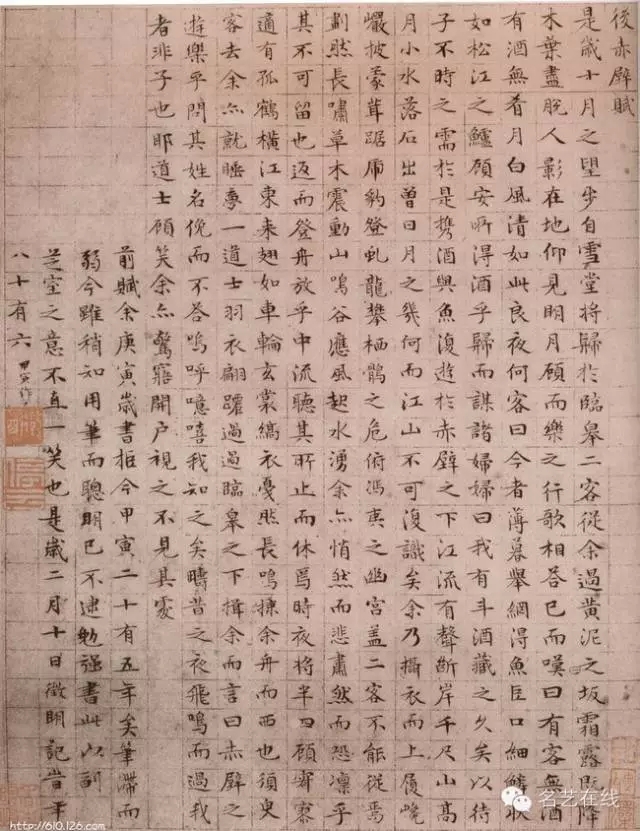
其实,千百年来,先人们用毛笔写字是有深意的,这里不妨探讨一下。
首先,毛笔柔软而有弹性。柔软多变化,弹性出生机。学书者要掌握毛笔,必先摸清笔性,进而随顺笔性,引领笔性,然后才能发挥笔性。而要做到对毛笔的摸清、随顺、引领、发挥,必先使自心清明、宁静、不固执。然后以心为主,以手为帅。主帅倡导于前,笔锋顺随于后,方能万毫齐心,锋转如意。而初学者,多数用心粗浮,刚愎自用,把毛笔看成肆意的工具,想刷即刷,要拖就拖,横突撞竖,无有忌惮。先人们正是想用毛笔给初学者以启示——“顺我者昌,逆我者亡”。顺着笔性,引领笔锋,则点画清雅有力。逆着笔性,绞结笔锋,则点画狼籍粗浊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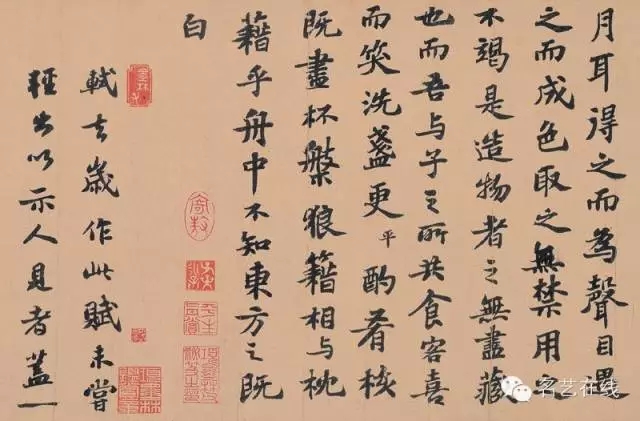
懂得毛笔可以调伏自心,我们对毛笔的态度就会有所改变。心欲畅,先令笔畅;心欲强,先令笔强,心欲使转无碍,先令笔锋使转无碍。说是以心用笔,实是由笔调心。论语云“毋意,毋必,毋固,毋我”,最能表达我们对毛笔的态度。如此用笔时不见我,而笔性即是我;用墨时不见我,而墨性即是我;用纸时不见我,而纸性即是我。推而论之,与万物交而无我,则万物之性即是我。我岂区区哉,我实天地万物之心也!毛笔给人的启示岂浅鲜哉?
其次,毛笔借水墨可显一切形体与色相。
老子云:“上善若水”。水无色可容一切色,水无形可成一切形,水无垢可洗一切垢,水之德大矣。而推扬水德,不遗余力的功臣,无过毛笔。世间一切有相形体,不外由点、线、面组合而成。点积成线,线积成面,面积成体。说是得体、得面,实皆由点积成。点有千形万状,不尽差别。只有毛笔柔软、弹力、灵活、多变的特性,才能借水墨淋漓尽致地把它们表现出来。进而或提按、或顿挫、或转折,把世间一切形形色色体现无遗。其间要粗可粗,要细可细,要长可长,要短可短,要干湿可干湿,要浓淡可浓淡,凡所须求,皆可体现。乃至一切蠢动含灵,人物禽兽,花鸟鱼虫,天飞地走,空飘水游,皆可应笔而成,栩栩如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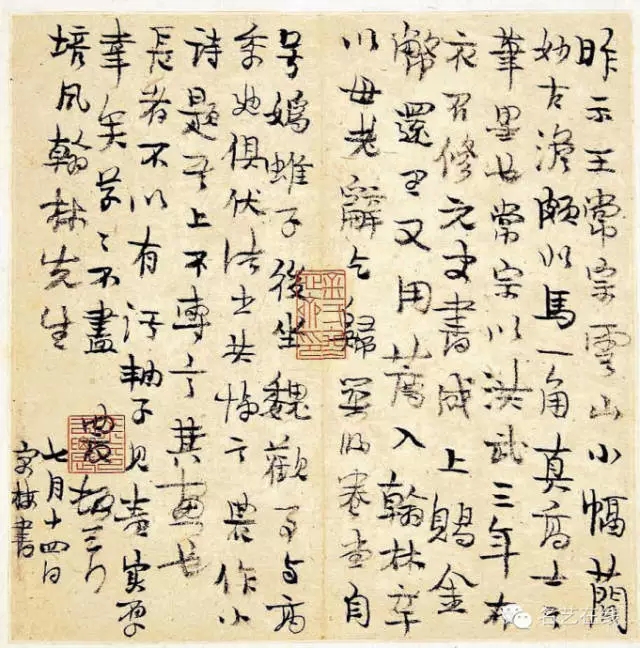
笔墨之德,岂可尽言哉!
然而笔还是笔,描绘了大千世界,抒发了千愁万绪,笔自己却一无所获。水与墨更是蜡炬成灰,随千言而化身,应万象以消己。笔墨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,不正是先人们代代颂扬的文明精粹吗?老子云“功成而不居”,笔墨是当之无愧的。
相比于毛笔的灵活、善现、无我执,硬笔则显得格外生硬、死板、无趣味。书写时,要粗粗不了,要细细不了,要浓淡,浓淡不了,许多因素都是硬性的,不可变的。因而禁锢了人的灵性。所以千百年来,先人们没有发明硬笔,而坚持用毛笔书写,目的是借毛笔这把“拂尘”,拂去学者心中的浮躁、昏昧与固执。
从而培养其安宁、清明、灵动的心理素质。
如上所述,学书者若能认识毛笔那无与能比的表现功能,认识毛笔无私无求的献身精神,定然会以崇敬之心,视笔为师,视笔为友,乃至以笔为心,舒展胸臆。久于其道,必能挥运自如,而得用笔三昧。
接前文,心手一如叫得笔,如何才能做到呢?
老子云:“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”。用书法来况喻。执笔在手,高举不下,谁也不知要写什么,自己也没动念,那就叫道。在道家学说里,此一念不生的状态,被认为是天地未分之前就有的,所以又叫先天大道。动了念,想写一点,此想写之念,便是“一”。“一”是无念状态的道所生,所以叫“道生一”,又叫“无中生有”。此“一”只是念,虚而不实。要让念落在实处,才叫得一。换句话说,想写一点是主观,一点既成是客观,主观与客观完全一致,叫得一。如果想写的主观与写成的客观有出入,不一致,那便成主、客对立,又名二元对立,又叫一分为二。一分为二即是一生二。有了二元对立,中间便产生了一个识别、判断的意识。如写出一点,是轻是重,是方是圆,心里了然分明。此了然分明的意识,生于主观与客观之间,排行老三,故叫二生三。“三”主分别取舍,而每一次分别取舍,又将产生新的二元对立,从而出现二生四、四生八、八生六十四,乃至生出百千万数,故而叫三生万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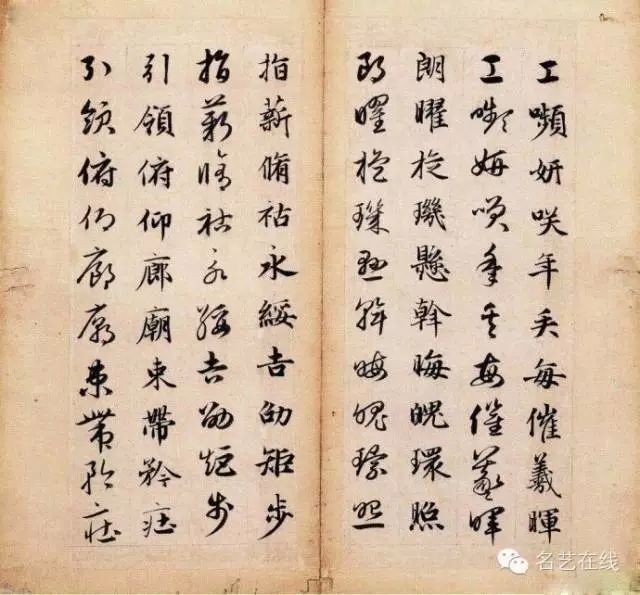
老子这段话,启示了我们得笔的窍诀——舍“三”守“一”。古德云:“至道无难,唯嫌拣择”,拣择是意识“三”的喜好,“三”的分别取舍往往会把“大体”丢掉,只抓着一些鸡毛蒜皮,最是祸害。因此要极力避免“三”的干扰,而直接用“一”。“一”是清净一念。一念既明,诸缘随顺。如捕蛇者,盯住蛇的“七寸”,则招招要蛇命。如放牛者,牵着牛的鼻子,则牛惟命是从。只是起念要纯,守持要精,念、守都在要害,才是真守一。用笔的“一”是什么呢?——是“点”。
点有轻轻一触之意。所谓“蜻蜓点水”、“凤凰点头”,强调的只一“轻”字。既是轻轻一触,必有横触、竖触、侧触、卧触,乃至百千种触。故点无一定形状,却有一定之理,此理即是“轻”。轻则灵,灵活的点触施以起、行、收等具体动作,便可将一切点画体现出来。兹说明如下。
起。人躺在床上,听人喊开门,第一动作是从床上起来,再去开门。同样,笔轻轻点在纸上,成点画之前,也要先起笔。起笔的原则是,意欲右而笔先左(横),意欲下而笔先上(竖),意欲左下而笔先右上(撇),意欲右下而笔先左上(捺)。如跳高,欲上腾,先下蹲。如出拳,欲冲前,先缩后。此理明白如火,只需心清手巧,皆可体会得到,关键在取势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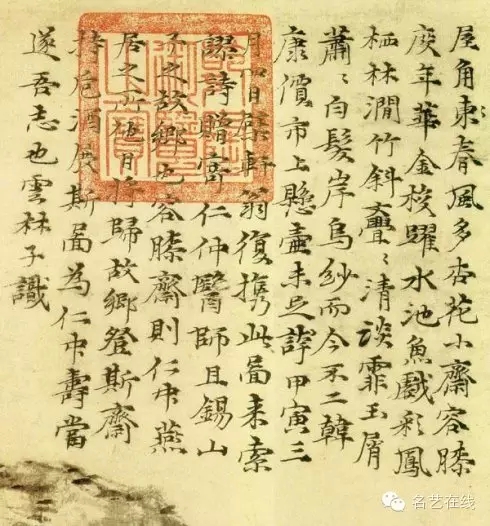
行。笔起以后,可匀力而行,可变速而行。可直线行去,也可加转折、顿挫、提按行去。关键在顺势。
收。点画行完,靠收来蓄势。收主轻提。原则是右行左提(横),下行上提(竖),左下行右上提(撇),右下行左上提(捺)。提分实提、虚提。对横竖需实提,收回行笔;对撇捺要虚提,收回行意。易经云:“无往不复”。形容收笔是最恰当不过的。
起、行、收囊括一切点画,最是得笔关键。
起以取势。正如万里鹏程,要在脚下一点。此一点若取势得力,则随势飘摇轻松自在。用笔亦同此理。笔在点纸时,迅捷取势,则所起点画,灵动沉着,遒劲有力。行以顺势。如顺水行舟,水直则舟直,水曲则舟曲,水有潮汐,舟有起伏。笔行画中,亦复如是。或提按,或顿挫,或转折,要在把握一“顺”字,不可逆势。势逆理违,必致线条僵死,而乏生机活力。
收以蓄势。蓄收笔中所顺之势,以启下笔。此最关键。如渔人打鱼。网撒下去,收拾不好,鱼会漏掉。同样,笔收不好,则所起、所顺之势,会应笔消失。既失本画完整,又害后画取势。所以得笔的试金石当在其收束处。
总之,起、行、收只要那轻轻一“点”有势。如果能随处落点取势,随处行去顺势,随处收束蓄势,则手中之笔,触纸皆有生气。如此,行笔在纸,犹如口中吐气。欲长则长,欲短则短,要急可急,要缓可缓,可婉转唏嘘,可气吞河山。总论归一心,呈相可万端,得笔之妙处,岂可尽言哉。